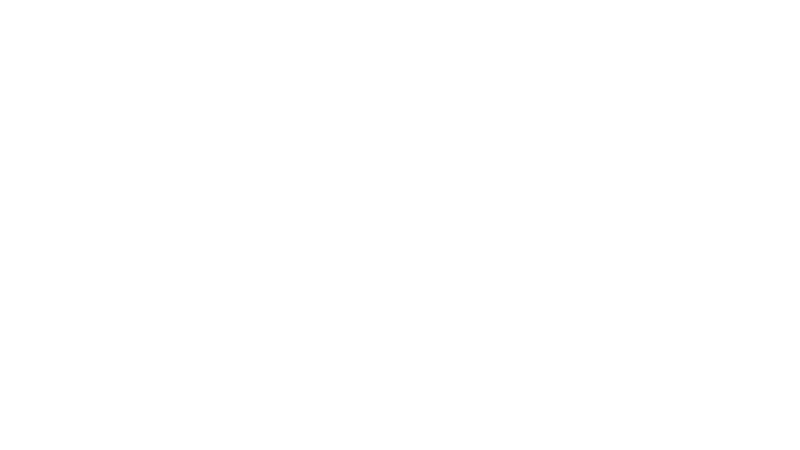他们把我全身上下接上各种各样的仪器,正因为如此,他们不容许房间太温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房间里好冷,让我的疼痛更糟糕。他们不给我止痛药。不过即使他们给了,在我那种情况下,也不能给太多。〔…〕由于寒冷,好可怕,好可怕。不只是让你痛苦,也会使你焦躁不安。而我应该要保持不动的,我应该保持不动。
因为他们把我全身上下接上各种各样的仪器,正因为如此,他们不容许房间太温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房间里好冷,让我的疼痛更糟糕。他们不给我止痛药。不过即使他们给了,在我那种情况下,也不能给太多。而且那个房间好冷,我偷偷用了些暖暖包,也被他们拿走。他们说:「不能这样做,太危险了。」他们担心我的血液过于沸腾或怎样,然后伤口会裂开之类的。由于寒冷,好可怕,好可怕。不只是让你痛苦,也会使你焦躁不安。而我应该要保持不动的,我应该保持不动。当你痛到很想跳出窗外到处跑时,怎可能保持不动?那就像全身都是蚂蚁在爬,而里面好像有东西不停在推挤你一样。那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。
(但您到底生了什么病呢,师父?)我不能告诉你。秘密。我从你们的一位师姊身上感染来的。一种很罕见的疾病。经由说话,因嘴巴太靠近而传染,我意思是唾液之类传染的。现在没事了。我意思是经过这些日子后,现在我真的没问题了。有时候我还是会痛,但是我知道没事了。我的健康状况良好。之前,我以为大概永远这样,我可能好不了了。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即使有吃药,那种疼痛也彷佛永远好不了。那是一种很难医的病症。很罕见。好,没关系,说够了。我不想告诉你们。
甚至曾经有一度,我要你们大家都要戴口罩。即使当时我知道,不过还是无法避免。不知怎的,它还是偷偷潜入我的生活,发生在家中。在这里我可以避免,但在家里有时就无法避免。他们就是这么做,就像这样。我也不想说是谁。我不想说。你们知道这些就够了。
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时光,得要隐藏身分,又必须住在医院,检查哪里出了毛病,然后又得接受手术,哪里都逃不了。如果我逃走,就得去另一家医院,而在那地区的另一家医院没有这方面的设备。为了一些特殊设备,你必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。而在那个地方一样也会有检查身分的问题。所以,每天我都在想:「也许这是我的最后一天。也许现在警察随时会冲进来,任何一分钟都有可能。我就等着吧。我心想该发生的就发生吧。我又能怎么办?」
总之我还是受到了保护,现在没问题了。他们(医院员工)当时对我大吼大叫,不过他们并没有做什么。直到最后一天,当我进去要付帐时,那位女士,在接待处的秘书,又再度对我大声嚷嚷。我说:「我只是要来付钱啊。」「但是您必须给我护照!」我说:「为什么?我没带来。拜托!我只是想付钱。」然后她又再对我大声说:「您住院时的模样跟您现在的模样不一样。」说了一大堆,我听不太懂她的语言。不过我知道她在大吼,这是肯定的。很大声,每个人都听到了。所以行政部门的主管—我猜他是主管—好像听见了。她吼得那么大声,几哩外的人也听得到。我能怎样,只能一直说:「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真的很抱歉,请原谅,我只是想付钱,付完就走。」然而她叫嚣个不停。连钱也不收。她只说:「我要您的护照。」然后她又找人翻译成英文和法文,不管怎样,一直告诉我:「马上拿护照来!」
然后不知怎的,主管把她叫进去,她带我和司机一起进去。我不知道主管对她说了什么,不过那个人看看我,然后对她说了一些话。走出来以后,她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。她对我微笑着说:「您何时会回英国?」为什么会这样?不用看护照,什么都不用!事后,她甚至还接受了我的礼物。之前她在想,我是个罪犯。因为我到哪里都会带着小礼物。她本来不接受。她有点…噢,她吼得好大声。啊,让我当下不知所措,只能不停地说:「对不起,对不起。」那时我很疼痛,病得很厉害,我全身到处都裹着绷带,她还是对我大声。我猜想那主管看了我一眼,之后为我这个「小女孩」感到很难过。我的司机他大约五、六呎(约一百八十公分)高。我很矮小,而他结实又强壮。跟他相较之下,我更显弱小。可能他好好看了我一眼之后,觉得「这个女人好可怜」—全身都是绷带,我连说话都难,还有腹部也痛,全身都痛,连走路也困难,却受到这样的叫嚣。
所以,他对她说了些什么,她带我出去后,态度马上转变。我当时好惊讶,也松了一口气,当然。我不知道他告诉了她什么。可能他说:「收下她的钱就是了,你需要做的就是这样。我们需要的是钱,对不对?有钱才能支付员工、医药、医生费用。」这就是他们需要的。干嘛要我的护照?最糟糕的应该是,要是他们不收钱,我就这样跑掉了。所以他说:「收下她的钱就是了。」也许是这样说的:「在她跑掉之前!」是嘛,若换作是别人,他们会假装生气、愤怒或害怕,然后走掉,永远不回头。但我太善良了,我甚至还再回去确定一切费用都付清了,因为后来还有一些后续回诊。和扫描,有时候扫描费用很贵。他们称作为T扫描什么的?(是CAT断层扫描吗?)不是CAT扫描。(CT电脑断层扫描。)CT扫描,扫描全身。你必须保持不动。首先他们把某种蓝色东西置入你的体内。一种蓝色药物,让他们可以看清楚。你必须先喝一点水。然后我甚至爬不上去那台子。而他们好粗鲁,就把你推进去。他们不了解你的痛苦。他们不知道我全身那么疼痛。他们无法了解。
而且,因为医生开错药,因此那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,疼痛仍然持续着。他们让我从这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,总是各式各样的扫描、各种种类的检验。然后把我放到这里、那里的床,我简直不能…我痛不欲生。我宁可死掉,因为疼痛到那种地步。因为他们还搞不清楚我的病因,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无法给我太多。只给我抗生素和止痛药,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作用,只是使病情更糟。让我的身体更僵硬,然后…真是可怕,我连吃东西或什么的都不能。而最糟糕的事是我还得担心身分的问题。我的确是受到保护,因为我躺在医院那么久…当然这当中,总共换了两、三家医院,但仍然在医院躺了至少好几个星期,但我还是很担心。
好,我们打坐吧,否则我得回家了。还有什么问题或故事吗?好让我能打起精神?等一下,亲爱的,是,说吧。(首先我要感谢师父,感谢您邀请我们,[尽管]有这一切…)邀请你们?我写邀请函了吗?(当然,我申请了,但是…[尽管]有这一切风险和危险的情况。)你身处险境?(我意思是,您…)啊。(是的,您必须来…)我已经习惯了。(太感谢您了。)只要我能来看你们,我不在乎任何危险。有时候我不能来,那才是问题。不是危不危险的问题,是不能来的问题。不客气。(是,谢谢您。)
(希望这是个有趣的故事。最近我领养了一位猫〔族人〕,不久之前,我和一些师姊救了他。我那时无法马上领养他,所以我就寻找其他人来领养他,但是没有人出现,没有人可以领养。)然后呢?(所以他显得有点忧郁。)所以现在怎样了?直接说结论,你领养他了吗?(我领养了。)好,那就好。我还在怕你把他丢掉呢。(抱歉。因为我希望他快乐起来,所以我叫他Happy,以您的狗〔族人〕命名,他就开始吃很多东西。)是吗?(是,像您的狗〔族人〕一样。)他很快乐!(是。)他胖吗?(是,很胖。)医生说他很胖吗?(是,他说了,他算是健康的。)他健康就好了。胖,没关系。
(但是后来我发现,所有其他叫做Happy的猫,他们都吃很多。)是吗?(是。)当然他们吃得多,就像我的狗族人。(是的。)尤其Happy,她吃很多,医生说:「要节食了。」好,我就让她节食,但是节食过后,她吃更多。她还是一样。或当我没注意的时候,去吃其他狗族人的食物。或她会出去乱吃东西,让我更担心。所以最近医生发现她有甲状腺的问题,所以她才肥胖,不只是因为食物而已。所以给她药吃,如今她很像模特儿的身材了。不过还是吃很多。(了解。)我吃的东西,她都爱吃,即使对她并不好。我说:「对你不好。拜托。不是我不给你吃,而是这东西对你不太好。」她说:「没关系。对您好的,就是对我好。」所以—她就吃了。有时我也为她感到难过,因为她就只有食物而已。她没有男朋友,什么都没有了,如今又老了,我也不知道她何时会往生,懂吗?所以来日不多,若她能享受,何不由她去?她爱吃,只要她还在这个狗族人的生命里,我希望她能快乐。也能享受生活,并非总是墨守成规,这个不行、那个不许的,以及…
狗族人的生活已经很受限制了,因为他们和我一起住,有时…我喜欢干净,所以我们得清洁他们很多次。每当他们外出后,我们就得清洁他们,他们才能进屋内。(了解。)因为他们会到处走动,上我的床、沙发,到处都去,如果我们没把他们打理干净,就会到处都是他们的爪印。爪印到处都是。所以我们清洁他们,也是为了健康着想。当然他们并非都喜欢被清洁。是有点麻烦—腿抬起来,要清洁四次。但是我设计了一种新的系统。我告诉侍者:「不用弄得太麻烦。」因为本来有很多位助手也就没关系,但是当只剩下一位时,我就说,不用太麻烦了,只要用醋水清洁过一次。然后再用水洗过,若可以的话;如果太忙,就不必了。只要有用醋水洗过就可以了。或是只要一到两天有用醋水洗过就好,不必每天用。其他天就用水就好,这样他们就很干净了。而目前我们是这样做的。当然,在狗族人进屋前,必须先洗过他们的爪子,因为会有泥土。(了解。)不洗的话,他们会把爪印弄得到处都是,我们无法一直清洗。也是为了环保—不断清洗的话,会到处都是很多清洁剂。况且水也很宝贵。所以由于这个理由,我们会帮狗族人清洁。因为如果不帮他们清洁的话,我们就得经常洗床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