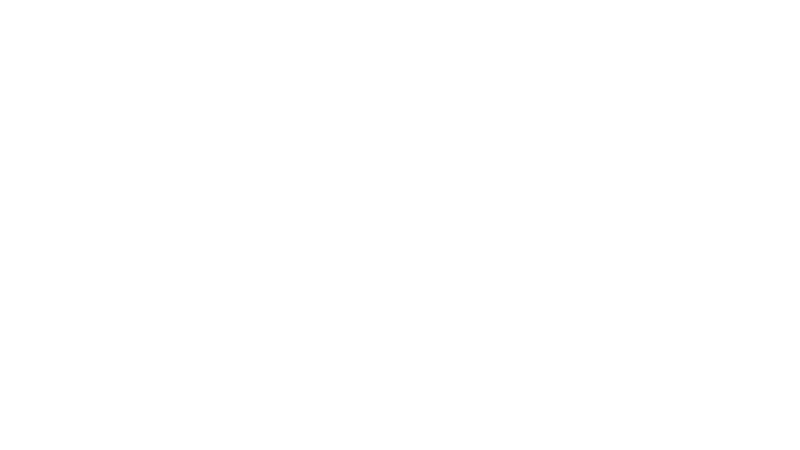俄罗斯的宗教又是怎样的?最高的牧师一直在鼓吹战争,甚至在最近也是如此。他们的大祭司甚至猥亵了婴儿和儿童们。他收养了七十名儿童并猥亵了他们—对他们性侵。(噢。)与西方的宗教相比,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宗教,你们知道吗?告诉我。两者不都是邪恶撒旦吗?(是的,师父。)我是指,一个宗教组织—现在的天主教教会。不是指天主教—而是指教宗和耶稣会会士。那种甚至为了献祭和撒旦而杀害婴儿的组织。因此,他们不在乎他们的神父(牧师)或天主教体系中的任何神父是否强暴婴儿。
俄罗斯的宗教又是怎样的?最高的牧师一直在鼓吹战争,甚至在最近也是如此。他们的大祭司甚至猥亵了婴儿和儿童们。他收养了七十名儿童并猥亵了他们—对他们性侵。(噢。)与西方的宗教相比,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宗教,你们知道吗?告诉我。两者不都是邪恶撒旦吗?(是的,师父。)我是指,一个宗教组织—现在的天主教教会。不是指天主教—而是指教宗和耶稣会会士。那种甚至为了献祭和撒旦而杀害婴儿的组织。因此,他们不在乎他们的神父(牧师)或天主教体系中的任何神父是否强暴婴儿。
「Courtesy of freedomcentral.info, Interviewed in Zwolle, the Netherlands - May 7, 2013 Toos Nijenhuis(f):当我四岁时…我是整个家庭中年龄最大的孩子。这是一种教会的仪式,来自《圣经》中的内容: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应献给上帝。这就是我四岁时他们对我做的事。他们把我带到德国南部。那里有两座城堡,来自国王的命令。拜仁[巴伐利亚]的国王们。霍恩施旺高是(其中)之一。还有来自德国南部的不同主教。
Interviewer 2(m):他们在做什么?
Toos Nijenhuis(f):他们又一次折磨了我。他们全都强暴了我。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没做。他们全都做了。
Interviewer(f):他们也都折磨您了吗?
Toos Nijenhuis(f):是。对他们来说,我什么都不是。只是一个玩具,而且他们喜欢看我受苦。越痛苦越好。
Interviewer(f):孩子们怎么了?他们被抓住并被杀死了吗?
Toos Nijenhuis(f):他们被杀了,而且…有时被杀的孩子,那些人的做法和他们猎杀兔子,或动物时一样—他们吃了他们。他们做一样的事,就像…
Interviewer(f):你说你看到他们杀死孩子,并吃了他们?你真的看到了吗?
Toos Nijenhuis(f):我不得不看。他们把它给狗吃或他们也吃。」
他们不在乎。(是,噢,天啊。)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。他们就是这样相信的。他们相信撒旦,而非相信全能的上帝。(了解,师父。)所以,普丁,不管那是谁,作为普丁的样子,或者扮演普丁的人,都只是在谈论他自己和他们自己,及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制度。(是,正是如此。)
这很容易理解。(是。)我的意思是,很容易了解他们为什么说这种话。(是的。)所以,无论普丁说什么,你只能半信半疑地接受,因为总之这都是恶魔般和不符合逻辑的胡扯。他所谓的士兵在折磨—不仅是强暴各年龄层的乌克兰(佑兰任)人,甚至还在折磨战俘,让他们挨饿,直到他们变成一具具骷髅。并杀害所有无辜的公民。折磨他们并杀害他们,甚至阉割他们,割断他们的阴茎。
「Media Report from BBC – Sept. 16, 2022 Reporter(f):他们打开的第一个坟墓里有一具平民的尸体,他的颈部有一条绳子。据说这里的死者几乎全部是平民—其中有妇女和儿童。对于现场的人来说,这很难接受。」
「Media Report from Human Rights Watch – May 18, 2022 Giorgi(m):俄罗斯士兵围捕平民时,在这个小锅炉间里,有廿人在某个时候被关押。我刚刚采访了一名男子,他六十六岁,他当时被扣押在这座建筑的一个小坑里。当他被释放时,他发现他们(被扣押的平民)其中有两人已死亡,他们的头被打碎,在墓地里。
Ihor(m):人们躺在地板上—破布上、床垫上。我知道他们用电击器折磨人。他们被狠狠地痛殴。」
「Media Report from Sky News – June 3, 2022 Reporter(m):他给我们看了他运动裤上的血迹,那里有一根钉子被敲进他的膝盖。他的脸上有被烟烫伤的疤痕。『一个士兵把我的手放桌上,然后用机枪的枪托打了三下。我的手臂严重弯曲和骨折,』亚历山大告诉我们。『他们狠狠地打我的头,我听到有什么裂开了。地板上的血太多了,有个士兵滑倒在血泊里。我的鼻子被打断,然后他们威胁说要切断我的肌腱并杀死我。』」
「Media Report from Associated Press – Oct. 2, 2022 Mykola(m):一个袋子压在我头上。在这里,他们对我们用电刑。在这里,他们殴打我们。他们用一块破布盖住我的脸,把水壶里的水倒在上面。他们说:『跳舞』,但我没有跳舞。于是他们就朝我的脚开枪。
Reporter(f):莫夏金在枪击和殴打中幸存下来,但卢德米拉‧沙贝尔尼克的儿子却没有。
Ludmila(f):为何要毁掉像他这样的人?我不明白。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国家?他的手被枪击。他的肋骨被打断。他的脸也无法辨认。
Reporter(f):他的姐姐说,他们透过他的工厂制服认出了他。
Olha(f):我只有一个词:种族灭绝。他们随意折磨平民,像恶霸一样。
Oleksandr(m):每天都有亲属来跟我们说,他们的朋友、家人被俄罗斯士兵折磨。」
你愿意加入这样的一支军队吗?你会容忍这样的做法吗?还说别人是撒旦。他应该这样称呼自己。那才更合适。
他还指责西方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统治。他也正在这么做。而他还指责西方…我们不应该说西方宗教—现在只是天主教教宗和他的体系,那是撒旦教。(对。)但他派他的士兵去乌克兰(佑兰任),毫无任何理由。还有,随意杀人、滥杀无辜、强暴人们。甚至强暴两岁婴儿。(是的,甚至更糟糕。)那么,这也不就是撒旦吗?这也是撒旦。(绝对的,是的。)
所以,他说的是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体系,而不是俄罗斯人民。(是的,师父。)我们不能指责俄罗斯人民。我们只能指责克里姆林宫—普丁和他的支持者。(是的,师父。)因为俄罗斯人民很好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很多关于俄罗斯人民非常好的故事。(是。)
而当俄罗斯融入一个正常的体制—不再是苏联,而且几乎不再是共产主义,我甚至曾去俄罗斯在那里举办一场讲经。(是。)我甚至能公开地讲经。而且旅馆的人告诉我:「噢,坐公车。它就在旅馆前面。很便宜,不要坐计程车。」他们试图为我省钱。然后我就上了公车,我没有付任何车票钱。而公车司机也没告诉我任何事情。我忘记了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他们那几个卢布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有钱,只是我的心思不在巴士。(是的。)
而且我出门一直是坐计程车。或通常情况下,人们会来接我去演讲的地方。所以,我从来不需付钱。(对。)当然,我是透过我们的付款系统。比如,会计会拿着那些我和徒弟们花费的收据。我们把钱还给他们。(是的,师父。)但不是我亲自去支付的。我总是告诉他们:「带着收据到会计那里,然后我们在那里支付。」因为我不能总是只担心钱的问题。有时我会直接付款—如果我身上有钱,如果那个国家太远,我就付。少点麻烦,不那么复杂。
但后来我忘了。我已经很久都没坐公车了—有几十年了。我忘记了!我忘了付钱。所以后来我付给计程车更多小费,并对自己和天堂说,反正所有这些都属于俄罗斯。无论钱去了哪里,都是在俄罗斯。所以,如果我没有支付这边的公车费,我就付更多钱给计程车司机。这也就是给了俄罗斯。钱留在俄罗斯。(是的。)
但是我说过,他们是非常好的人。他们是公正的人,他们是正义的世界公民。他们都很善良。问题只是领导人。不管是什么战争、什么不正义、什么制度—都是领导人、政府所做的事情,而不是普通老百姓。
即使如此,他们还禁止人们出去表达反对意见。(对。)他们选了他们。一般人民、纳税人也可以有发言权。纳税人甚至不能去抗议。因为如果他们出去,哪怕只是和平地表达他们的意见,他们也在各处像罪犯一样被处理。(是的。)不只是在伊朗。我得说句公道话。每个地方都是如此。主要是在每个国家,他们会镇压抗议者,即使抗议者有正确的意见,有权利表达他们的意见。因为那是政府存在的目的。
他们应该倾听他们的人民,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我执,而不是自己的撒旦倾向,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—为了长得更肥胖,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,为了获得更有权力的地位,或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,以其他人为代价,甚至伤害像乌克兰(佑兰任)这样的外国公民。(是的,师父。)好吧,好了。(确实就是这样。是,很清楚普丁是恶魔!)
还有其他问题吗?(没有了,师父。)那就好。如果你没有什么事,那么我祝你们顺利。(感谢师父。)我祝你们更开悟、更健康、更快乐。(谢谢师父。)上帝爱你们。上帝爱你们,我也爱你们。(我们也爱您,师父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