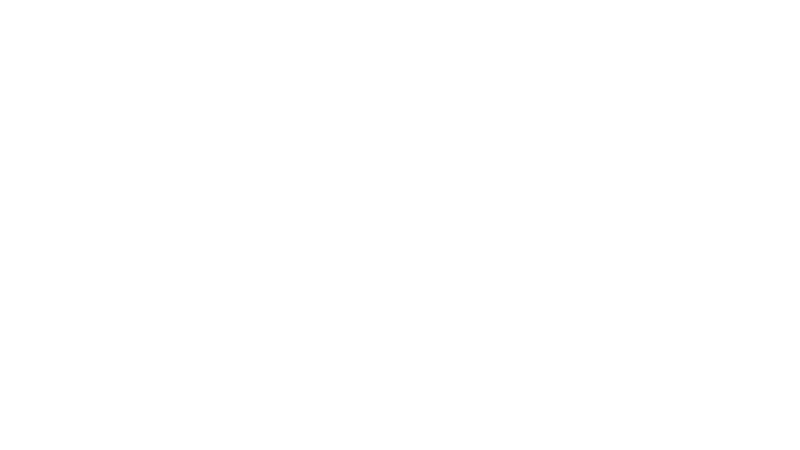请和我一起拯救世界。帮助那些受苦的动物,他们无依无靠,没有人保护他们,他们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声、吶喊。我每次都无法忍受。
我当时在阳明山上,那是国家公园,景致很美,遗世独立。那时我住帐篷,天气十分寒冷,冷冽无比。觉得山好像不是很高,因为车子蜿蜒而上,坡度缓缓上升,所以到达山顶时,不觉得山很高。山顶有些地方很平坦,所以很久以前,这山上就有人盖房子。现在当然不准再盖,因为变成国家公园了。地势很平坦。我在阳明山有间小屋,勉强称其为屋子。开车抵达山顶之后,还得再走一大段路,然后爬阶梯上去。我不知道共有几千阶,至少有几百阶吧。之后要再走一段路,再爬阶梯,再走一段路。我不记得要走多久,也许至少要…有没有人记得?(二十分钟。)从下面。从自己厅屋顶。二十分钟是你们走的,我走的话,最少四十分钟。我刚才问你们的台湾(福尔摩沙)师兄,他告诉我要走廿分钟。但我们已经在山顶了,还要再花廿分钟走上去。我说他走的话花廿分钟,我可能要走三、四十分钟或一小时。有的助手说要走一小时,因为她途中会休息一下。
那里真的空无一物,但那是一大片平地,对我而言够大了。山上还有平坦的竹林。台湾人(福尔摩沙人),台北同修令我很惊喜,他们盖了六角形屋子,卧室在上方,很隐蔽。楼下还有一个大空间,对我而言当然够大了。我很娇小,所以他们盖什么都够大。那小屋像一座凉亭。有时你们会在我的烹饪节目中看到,或有些节目介绍我作画的那个凉亭。凉亭上方有间小卧室。他们还在屋顶上安装一个洒水系统,他们很有爱心。你们的一位师兄,他已跟家人移居澳洲,他跟台北或其他小中心几位师兄和师姊,一起建造那座亭屋。但主要是他在处理,他是营造商,所以会盖。
他们在屋顶装洒水系统,因为他们有一次听到我说我喜欢雨。那就是他为我安装的神奇下雨系统。夏天也有助屋顶降温,所以我们没有冷气。我不记得有冷气。我们有电扇,我在凉亭煮东西。凉亭一片通透,没纱窗、没门,毫无遮蔽。我记得有蚊子,那片竹林里有好多蚊子,不过,蚊子从不叮我。我不记得我身旁的助手曾经被蚊子叮咬,但是我看到蚊子。哇!蚊子成群结队,密密麻麻,竹林各处都有。我看过。不过我只看过几次,我没怎么注意蚊子,因为他们没来吵我,很奇怪。如今在城巿或任何地方,蚊子却会咬我,奇怪。不晓得是我的血变甜了,或我的业障更有吸引力,可能两者都有吧。
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。以前我上去那里时,当时徒弟还不多。我为了难民的事在那里工作,后来就下山了。我为了帮助难民,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。我很不想离开那地方。我在那里,觉得自己超然物外,无欲无求。那是很简朴的地方,只有一个卧室。我不记得我有床,就睡在地板上。他们还接了水管供水,连电都接了。你们相信吗?
这群人神通广大。我还记得他是营造商,家境富裕。他们不能供养我金钱,因为我不接受供养,所以他们就上山帮忙。我想那个地方是私有地,我忘了问。我想应是私有地,因为那里种了竹子。有一大片竹林,也有其他各种果树。这些是国家公园成立前,人们在很早期就种的。当然,政府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农耕或种植,或建造小屋。但他们不能盖大房子,不能用混凝土和水泥等建材盖房子,但是可以盖小木屋。我听说,现在,那里的小屋年久失修,台风把一些地方吹坏了,他们想上山去修复。不过我说:「何必呢?路途遥远。搬材料上去很困难,所以算了吧。」我想我不可能还会有闲情逸致,再去住那里,我不希望他们浪费时间。用那些时间打坐就好,我这么跟他们说。
我不确定这段期间,他们有没有偷偷去修建,当作纪念馆。为后人保留,我归天以后,或许他们会卖门票,让人上去参观。「清海无上师,以前住过这里。大家看,这是她的鞋子,那边是她煮饭的地方。」大家都是这样导览已故者的房子或住所。我想像大概会有一群人,沿着这些难走的阶梯,往上走一大段路,抵达后就顶礼膜拜,拍照或四处触摸祈福。也许他们会为我塑像,立在房间的中央,欢迎游客。开车抵达山顶后,要再步行往上,走二十分钟的山路,离停车的地方很远,因为车子无法上去。要上去必须爬很多阶梯,之后才能继续前进。
我以前在那里有小仓库,两米乘两米。他们用几片铁皮围起来,用铁皮围出一个空间,上面再放屋顶。我曾住在那里,旁边是一条小溪。那里有一条小溪,那是我最喜欢的。那时候我的钱不多,我们买下那块地,跟一位师兄借了一些钱。我已经还给他了,他不想收,但我还给他。我说:「我不收任何供养,请收下。」钱不多,买那个小地方,所花的钱很少。依规定不可盖建筑物,他们用几片铁皮拼接,盖出一个正方形的空间。上方覆盖几张铁皮,随时要拆都很容易。我们还有一个大遮阳帐,用帆布、竹子和手边的材料所搭建。当时我们已开始工作。
那时我们只有一小群人,但已经在工作。我们分发传单,或小开数的单张新闻,给大众或同修,让他们继续研读教理,且继续获得启发和鼓励,坚持打坐和持纯素。当时是素食。我从不喝牛奶,那时没想过喝牛奶不好。后来看到乳牛饲养过程,竟如此骇人、残酷不仁,乳牛被圈禁在狭小栅栏,连转身都不可能,还被链住等等。噢,天啊!从此我不准徒弟再喝牛奶,即使牛奶可能被视为素食。牛奶虽非杀生取得,但乳牛被对待的方式,非常不人道。跟我以前在故乡所看到的完全不同。在悠乐(越南)人们不会那样对待牛。母牛或公牛在田野漫步。或许他们要帮忙粗重的工作,偶尔在农忙时节,帮农夫载运重物或犁田。他们有自己的牛舍。他们会回牛舍歇憩,牧牛人早上会来,带他们出去放牧。牛只多数时候很悠闲,吃得好,被照顾得很好,因为偏乡的农夫,生活仰赖母牛与公牛,所以待他们非常好。从来没有任何殴打或强迫他们的情况。跟我之前所见不同。
我在印度时,看到牛可以像人那样四处走动。要是有头母牛或公牛,正好在街道中央,甚至在高速公路上小憩,路上的车都会停下来。这你们都知道吧?即使不曾见过,也在电影里看过,我曾亲眼目睹。我到印度任何地方,牛就像人那样,备受尊敬与爱护。印度民众甚至会触摸牛的脚或臀部,再摸自己的额头,以示敬意。因为在印度,根据印度教的信仰,乳牛很神圣。他们为孩童供给牛奶。在以往没有多少设备和替代品的年代,乳牛供牛奶给许多孩童,把他们养大。因此,在印度,人们视乳牛如乳母,像第二个母亲。至今仍是如此。我在印度的时候,人们是如此。他们手边有什么食物,也会用来喂牛。他们有时有一些料理剩下的蔬菜,他们会扔到街上,牛会来吃。牛可以自由地四处漫步。人们还得让路给他们,而不是他们让路给人。所有车子都得停下来,直到这群母牛或公牛,休息够了,起身伸展,悠闲地踱步到隔壁,或邻近街道旁的草地,在那吃草或躺下为止。我所看到的是这样。
所以,我从没想过牛奶会造成什么伤害。此外,以前我曾研究佛教,佛陀第一次出定时,身体非常虚弱,因为他遵照别人所教的一种极端的修行方法。据说修这种法门的人,必须让自己彻底挨饿,不吃、不喝,只要打坐就好,就会到达涅盘。后来,佛陀了悟到那种方法不对。于是他放弃那个法门,后来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妇女,她给了他一些牛奶喝,使他得以恢复体力,继续学习和修行。因此我才认为喝牛奶并无大碍。但是后来,当我看到现代畜牧业,是这么惨无人道、邪恶、可怕及野蛮,我们当然不再喝牛奶了。倘若你们有人还不懂我说什么,请务必要看这些影片:像《统治》,善待动物组织的影片,要看《地球上的生灵》及《奶牛阴谋》。我们在无上师电视台免费宣传这些影片。也可透过「网飞」观看这些影片。在这类影片中都可看到人类如何无所不用其极,对无辜、无助、毫无防卫力的温和动物,极尽残暴虐待之能事。播给你的朋友们看,和他们一起看,就算你会哭也要一起看。纵使你因看到动物受苦,不禁失声尖叫,也要与你的朋友一起看。
那些仍然吃肉喝酒,甚至酒后驾车的人,你播放相关下场的影片给他们看。我知道画面怵目惊心。我无法看了而不尖叫。有时我得分好几段,才能把影片看完,以便告诉你们。也才能吩咐工作团队,要在无上师电视台宣传这些影片。我们不会完整播出那些骇人画面,因为对孩童而言太敏感。但会宣传影片和片名,让大家自己找来看。如此你们就能自行播放给其他人看。不要只靠我一个人,不要只靠无上师电视台。因为在某些角落,人们并不知道有我们这个电视台。不要依赖我们,别依赖我一个人救世界,你们和我一起拯救世界,好吗?(好!)
我说过有五十三%来自明师的力量,经由讲经,经由她赋予主播的能量,还有经由诸神的加持。无上师电视台便是以这种方式加持世界。海洋中每滴水都很重要,涓滴之水汇流成洋。所以,请和我一起拯救世界。帮助那些受苦的动物,他们无依无靠,没有人保护他们,他们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声、吶喊。我每次都无法忍受。我必须多次关掉理智,不然我会整日以泪洗面,痛苦万分,因为知道动物受苦受难。
我必须关闭某些感知,否则就无法工作,无法为无上师电视台工作,无法为你们工作,无法为这个世界工作。我必须坚强起来,但我并非总是那么坚强。我常常在我的房间,在山洞的一角暗自痛哭,只为释放一些苦楚。我不知不觉潸然泪下,泪流满面却不自知。恳请大家帮忙,竭尽所能帮助动物。让你的朋友知道畜牧业可怕骇人的行径,了解人类何以渐失人性,失去仁慈的品质、失去爱心、失去同情心。失去爱心就失去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