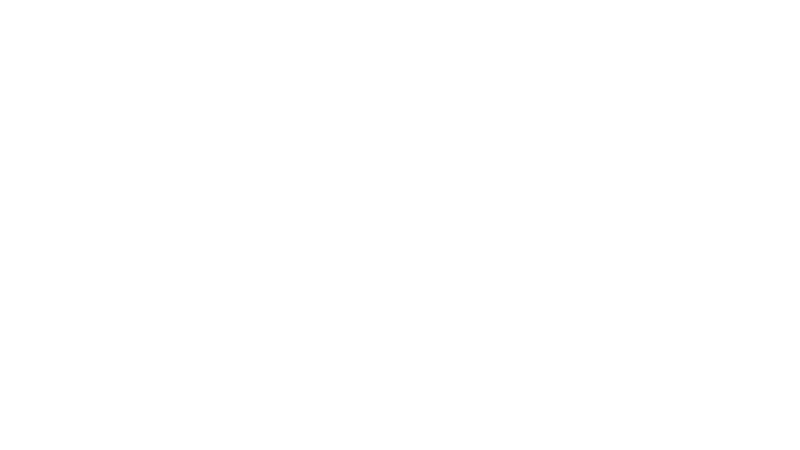當我在印度的道場時,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麼。因為沒人在做事,所以我就做了。我打掃庭院,幫植物澆水,打掃屋子,清洗階梯。把兩、三個水槽中滿滿的碗盤洗乾淨。因為每個人都追師父去了。或是坐得像個佛似地。我工作,是因為沒人工作!像這樣的兩個大水槽—他們為大眾做了大水槽—像這樣的兩個水槽。堆滿了,滿到…堆高起來。堆滿了碗盤。他們吃完就丟進水槽,然後大家都去追師父了。[…]
如果別人一天可以打掃四十間房間—整間都打掃,我意思說包括更換床單、擦亮浴室和清洗廁所,讓一切就像新的一樣…不是像我們在家裡那樣偶爾打掃一下,然後一星期再大掃除一次。不是那樣的。飯店必須要完美,尤其是一流的飯店。四星或五星級的,就必須那樣做。所以,不能說人手不夠。我又沒期待他們每天打掃二十間房間,當然沒有。但是每天兩、三間,那每間房間就會保持得乾乾淨淨。同修不管什麼時候來,都會有房間可住。
我說:「像這樣,他們來住,他們會生病的。你們會想住這樣有味道的房間嗎?」你們的房間有味道嗎?告訴我實話。(沒有。)有任何味道嗎?(沒有。)有霉味嗎?沒有吧?你們怎麼都不說話?你們在保護他們。我要他們打掃,但還沒有時間去檢查。不過我想他們做得很好。(好多了。)是嗎?(好很多了。)好很多了?(是的。)只是比較好而已?噢,你看過之前的樣子,對嗎?(是。)什麼時候?(也許…)一個月前嗎?(兩個月前。)所以那時很糟糕吧?你住進來時,必須自己打掃嗎?(不,不用。只是覺得有霉味。有味道。)是,我知道。(是潮溼的關係。)是,是,是。
因為沒有在天氣晴朗時,把門窗打開之類的。我們什麼都有。甚至有空調,所以如果你打開空調—輪流把空調打開,這裡開兩、三個房間,那裡開兩、三個房間,必要時就開—味道就不會太糟了。或打開所有的窗戶,好好打掃,就不會這樣了。或更換床單等等。所以現在你們知道了。所以上星期我回來這裡時。檢查了一下—噢,我只看一間就知道其他房間是怎樣了。兩間,我看過兩間房間。我就曉得了。連我的辦公室也是,也有很難聞的味道。聞起來像是很多年沒人打掃了。是啊,真不可思議。
所以我告訴你們,不要說你們沒時間打坐。如果有時間,你們也不會做什麼事。打坐不怎麼好。還會睡成那樣。事實上,因為你們在外面工作,回到家會更珍惜自己的時間,甚至打坐得更好。你會更加珍惜,更渴望打坐。有很多時間的人,他們什麼都不做。連打坐也坐不好。所以他們等級才依然很低。甚至屬於低等的肯定,還談不上低等級呢。
這裡有位長住,我不是在他們背後講他們。我說:「你說『不夠人手』是什麼意思?你要我在這裡留多少人?」你確定只有六個人嗎?至少八個人。我意思是,我們這裡已經有八個人或十個人。我說:「你要我在這個旅館再增加多少人?」我們可以用的房間只有二十幾間。十個人已經佔去了十間,因為沒有人在這裡,所以他們就佔用了房間。所以如果我叫更多人來這裡,那整個旅館,整個小中心滿滿的清潔人員、割草者和採橄欖者。就再也沒有房間給同修了。那這個小中心又有什麼用?就失去我們的目的,對嗎?我們必須把房間打掃乾淨,清空給同修來這裡享用。
我告訴他們,當年我在印度的時候,在當所謂的徒弟的時候,每天打掃庭院、打坐大殿和通往大殿的階梯。當時我打掃得很高興,覺得很榮幸。因為我想著的是,我在為聖人們打掃階梯。當時我是那樣想的。我一邊哼著歌,一邊打掃。怎麼會有人抱怨不夠時間打掃,不夠人手打掃呢?如果再加更多人手在這裡,那你們要住哪裡?只有工作人員住在這裡?我買一間旅館就為了給工作人員住!還沒提到愛家的工作人員,那裡也有六個人,對嗎?(是。)
所以有多少人已經住在這裡了?至少有十四個人。我們只有二十間房間可以使用。又有六間給你們住去了。真是多謝你們了。但仍然有氣味。不,這不能解決問題。不,不能。所以我告訴你們,不要以為,好,你當長住了,就沒事情可以做。你是有事情要做的。卻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做。每個人都只是來說:「噢,師父,我愛您。」如此而已。然後我就得包辦所有事情。只是愛我就好了。我不確定你們是否真的愛我!我對他們說:「因為如果你們愛我,就該做會讓我高興的事。我卻沒看到你們做了什麼讓我高興的事。除了你們必須做的,或我要你們做的事。其餘的,你們都不做。」
當我在印度的道場時,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麼。因為沒人在做事,所以我就做了。我打掃庭院,幫植物澆水,打掃屋子,清洗階梯。把兩、三個水槽中滿滿的碗盤洗乾淨。因為每個人都追師父去了。或是坐得像個佛似地。我工作,是因為沒人工作!像這樣的兩個大水槽—他們為大眾做了大水槽—像這樣的兩個水槽。堆滿了,滿到…堆高起來。堆滿了碗盤。他們吃完就丟進水槽,然後大家都去追師父了。所以,做完辦公室的事,幫忙回答信件之後,我會去廚房把那些疊得很高的碗盤洗好。而且感到很高興,有機會為大眾服務。感覺非常非常舒服。
不過印度徒弟不一樣,我告訴你們。當我在印度的時候,當然,我跟你們都一樣。有時會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,住在其他徒弟的家。噢,那個人好高興,好高興。他說:「哇,有機會透過侍奉您來侍奉師父,真好。請進。請原諒我們寒舍簡陋,不過一切都供您隨便使用。告訴我,您想要住在哪裡。全部都是您的。」他們煮飯給我吃,他們打掃屋子,還要洗我的衣服,擦我的鞋。噢,天啊。好高興有機會能透過洗徒弟的鞋子來侍奉師父。是!他們很神聖,我告訴你們。我那時也有同樣的感覺。
在其中某個道場,師父有一個祕書。而她很…她是德國人,抱歉。我只講了德國男人,不知道德國女人如何。很…不過她很愛師父。噢,她非常…噢,她佔有慾很強。不過我感到,因為她侍奉師父,如果我侍奉她的…因為她…你們知道的,認為師父是她的,沒有人可以侍奉師父。有時我覺得師父講話很多時,聲音好像沙啞了一樣。因為他去外面講經,回來又跟我們講話。所以我去廚房做點檸檬汁,加點糖,端給他喝。他很喜歡,她卻說:「不要再給他檸檬汁了。」我說:「為什麼?」「你不知道他要什麼!」我說:「他很喜歡。都喝光了。」比方說這樣。佔有心非常、非常強。也許我應該先得到她的許可,但我沒想到。我說:「他也是我的師父呀。」「為何只有你可以侍奉他,別人就不行?」不過我不是經常那麼做,只有偶爾。
或例如當他走過去要坐下來,他們並沒給他適當的椅子時。德國人,他們坐了他的位置。例如,他們有準備座位,但不像這樣,不像這樣明顯的。他們只是在屋子中央放了張小沙發。有一個德國婦人走過去就坐上去了。所以,師父沒地方可坐,就坐到其中一張印度吊床上。印度吊床像這樣:有個框架…抱歉!那真的是一團德國人。不,那位師父受許多德國人喜歡。那位祕書也是德國人。所以他們是很「一切按照秩序,井然有序」的。一切按照秩序,井然有序。所以那種印度吊床就像這樣:有一個木頭框架,然後用像是椰子做的繩子編織而成。這樣,這樣,懂嗎,就像這樣子。於是那個框架—當靠近…親愛的,你們知道吧?靠近框架處比較高。中間則凹下去一點點。
所以師父坐上去後,他就變成這樣。我替他感到難過。我想去拿…我應該把那個婦人從椅子上趕走才對。但我不習慣像那位德國祕書那樣行使威權。而她當時又不在那裡。那是我唯一的一次陪同這位師父。所以我從別處拿了幾個墊子為他墊著,讓他坐舒服一點。我就那樣做了。不過通常我不敢做這些的,因為一直都是她在做,只有那次她不在場。所以我才有機會,不過我當時仍然在想:「噢,我該做嗎?」「可以嗎?」懂嗎?因為已經習慣於…被要求不可以做…不過我為什麼講這些事?之前是講什麼?(印度徒弟是什麼樣子。)啊,印度徒弟是怎樣的,是!
不過印度徒弟從來不會跟師父坐在同樣的高度。你們想要的話是可以的。只是在這裡,我得坐高一點,你們才能看得到我,如此而已。佛陀的戒律也是如此規定,菩薩與出家人,不可以坐臥在高廣大床上。當然,如果像這樣的大眾聚會,每個人都帶他們的特大號床來,你想會變成怎樣?旁邊的人要坐哪裡?在那個時代,大多數印度貧窮的人,他們甚至沒有什麼床,都坐在地板上,也睡在地板上。反正那邊天氣炎熱—那樣比較涼爽。所以佛陀不讓出家人或任何人坐在高床上,如果他們要來打禪,不可以坐在高高的床座上。所以就成為一種傳統。不過這很合邏輯,不是嗎?
因為佛陀走到任何地方,一定有很多人追隨他或來看他。如果每個人都從德國帶來這麼高、這麼大的床,那就沒有人能看得到佛陀了。所以才有那種戒律。並非因為如果你坐上去就會死掉或怎樣,不是這樣的。另外也有一條給在家弟子的戒律,意思是要來打禪的人,想要當幾天聖人的人,必須自己帶吊床來。他們稱它為繩子床,吊掛的床。就是現在的吊床。記得你們以前去(台灣〔福爾摩沙〕)苗栗時,我們什麼屋頂都沒有—沒什麼屋頂,很小—所以大家都掛在吊床上,包括我自己。我們那時好棒。我好喜歡那樣。
通常我不喜歡大房子。感覺太大了。我不曉得,也許我個子很小。在較小的空間感覺比較舒服,我才比較好專注,而且也比較溫暖。就不需要很多電暖器,或不需要擁有很多東西。很簡單。幾秒鐘內,就把屋子打掃好了。其實,我也不曉得。我在山洞裡很快樂,但如果有間房子有很多的靈性能量,那我就只好住進去。就不會管那是在何處了。但如果可以,我更喜歡山洞。我更喜歡小床或較低的床。只是個人偏好,並非因為是出家眾戒律或什麼的。那樣會覺得比較涼爽,也比較輕鬆。